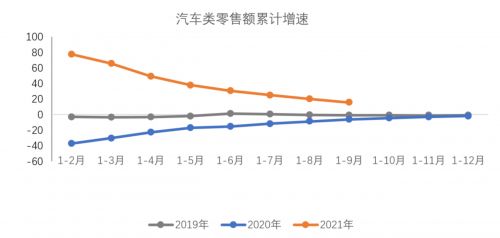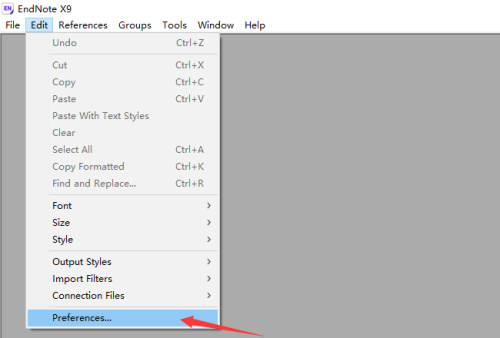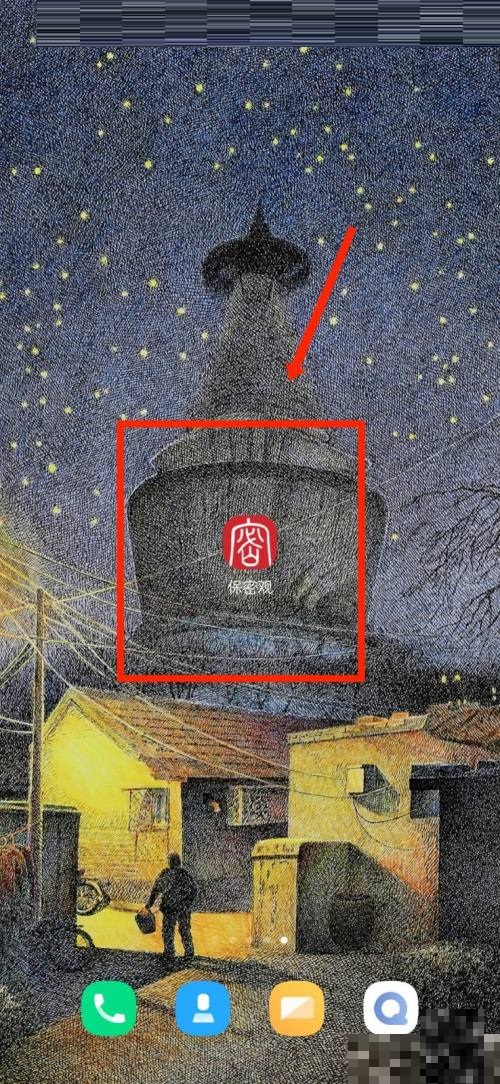01 阴沟
三四十年的光阴在历史长卷上几笔带过,许是平日里见惯了那些达官贵人给“洋面孔”卑躬屈膝惯了,北平的百姓都对“民国”这个新鲜词儿闭口不提。
那条死胡同一直印在我记忆里,银古街48号,胡同底最后一家便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,母亲从来不告诉我这个家是谁留下的,和我打听父亲的下场一样,多问几句免不了一场毒打。和我们一样,周围的邻居全是些穷苦贫寒的小户人家,像是提前商量好得一样,门窗瓦檐永远破烂着,院墙边上杂草疯一般的长着,一股死气竟像是带来了救命的雨水般,看似干燥的院墙上爬满了霉点,谁都不愿靠近,几间屋子连在一起又好像被有意地隔开,像一群聚众乞食衣衫褴褛的老乞丐,却推搡着互相嫌弃。胡同常年散发着一种特殊的腐烂气息,本来没有堆放垃圾的地方,渐渐被扔出了一条陷进黄土地里的阴沟,常年都塞满了腐烂的菜头、破布、各种不知名的赃物,太阳一晒,一股强烈的秽气便冲了上来。夏天更甚,偶尔下场大雨,一沟浓浊污黑的积水带着烂泥和秽物移动,之后阴沟又低了许多,谁也不知道这些秽物到了那里,是被泥地腐化了,还是被蒸发了,又或是飘到其他死胡同里了。冬天强了不少,虽然垃圾堆得山高,却没有一颗颗绿油油指头大的红头苍蝇,来年,阴沟也总会变平的。
闲来无事,我会跑到胡同口转悠,却逃不掉那股秽浪,那些住在胡同里等死的糟老头子好像也想逃离什么一样,每天都要搬个小凳子在固定的地方坐下,在我看来,那一张张面孔都长一个样,黝黑的脸上眉眼拧在一起,皱得让人分不清,一个个黑里透亮的宽额光头倒是显眼得很,破旧的长衫一径拖着,和那似留非留的散辫子不搭起来,任身上脏成什么样,那几绺头发油亮飘逸得很,和那青亮的头皮很是搭配,就像是细心呵护过想要挽留些什么,非要找些不同的话,除了辫子的长短,那便是这些糟老头子,有饿得头发昏的肥耗子,也有饿得皮包骨的干耗子。每次散场,总有那么一只唉声叹气地撂下一句话,“大清亡了,天子脚下也不好讨生活了。”然后便各自钻回窝里去了。八岁以前,我常能与他们碰面,可还是没能把他们的脸和窝对上号。不知算不算幸运,不管母亲对我多么厌烦,她总会把我收拾得干净利落,让我和那群正在长大的,同样脏污的小耗子格格不入,这倒是我为数不多想到能拜谢她的地方。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八岁以后,母亲就很少能和我碰面了,每隔一段时间,我早上醒来都能看到枕边有几枚罕见的湿哒哒的大洋,像是专门被洗干净了一样,这几枚大洋好像是走出阴沟的通行券,又像是驱逐符,我早早地背着布袋出发,一路逃出死胡同,新式学堂里能出得起学费的都是官富人家的子弟,起初我还天真地找寻我的同类,后来我便安分了起来,给自己又盖上了一层遮羞布,希望能遮住些腐秽气息。
初级中学没上完,我便被退学了,再回那条阴沟里不过是去受那几枚大洋,我没想到的是,母亲离世得那样早,我最后一次见到她,她好像等了很久一样,母亲站起来,一身羊毛长袄把她裹得严严实实,活像靠在墙角竖着卷起来的地毯,那袄子普通百姓是见不到的,我却并没有对母亲身上任何的华贵物件感到奇怪。
萎黄的面色在黯淡的光线下透不出一点亮来,两颊的肉像是被生生挖了去,连带眼窝的肉也剜了些,我尝试把她描回记忆中的模样,我失败了,眼前的人让我想不起来那冠绝“丽月楼”的风姿,只有腥红的唇色和乌黑的眼溏里躺得那对美眸撑住了美人的倔强,尽管母亲站起来只能够到我的胸膛,我还是被她常年来对我散发的怨毒气息吓得站不住脚,我没有伸出搀扶的手,我从她眼睛里看到了恨意,憎恶,嫌弃,像极了我看那阴沟里黑水时的眼神,她费力地抬起一只胳膊,把一只金怀表放在我手里,蜡黄的皮色蔓延到手上,那总是戴着钏子晃来晃去的精巧小手俨然已经成了一只鸡爪,蜷握着,连简单的屈伸动作也做不利索。
“你爹陆辛傅,在粤军当兵,去找他吧。”那么些年,我又听到了母亲冷到极点的声音。
我冻在了原地,母亲倒是飘回了冰冷的发着霉气的火炕上,我打开怀表,眼前陌生的男人穿着制服,身上的配件却很少,想是没拿过多少功勋,一条皮带斜拉在胸前,特制军帽下俊秀的眉眼含满了爱意,母亲依偎在他身前,披上了西洋很流行的网口白纱,白绢点着梅花的旗袍勾出她曼妙的腰肢来,一只雪地里的花鹿精灵再次浮现在我眼前,那对灵动的大眼睛好像只装得下一个人,我想他们大抵是爱得深沉的。
我长得竟很难看出那个男人的影子,只有眉眼处能看出点相似,偏我的眼神又那么凉薄,小眼镜总是盯着我的眼睛用日本话骂:“可恶的小偷。”“米龟啦希扭哆宝。”,我一时想不明白他是在骂我还是骂照片里的男人。
母亲很少正眼瞧我,像是厌恶这张长得越来越像她的脸,连咽气的时候也要背对着我,我想她定是恨极了我,小眼镜提着满满当当的菜回来了,他跪在炕前,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哭得那么伤心。
小眼镜和我帮母亲收拾身子,穿新衣的时候,我才看到母亲身上大片大片溃烂溢脓的疮口,假如真的有神仙,她大概是连母亲的皮相一起拿了去,我希望那仙人魂里住得也是母亲。
“丽月楼”的玉皇大帝们大概忙着去找那些魂儿了,母亲的黑棺材前竟然留下了那个被母亲嫌弃了一生的日本人小眼镜。
这一年冬天北平的雪来得出奇得晚,我赶在初雪之前上了山,跟着人群来到了战火纷飞下异常热闹的佛寺,大抵是寒冬的缘故,人挤着人,肉磨着肉也捂不暖殿内的冷气,一尊巨大的佛祖雕像坐在殿中央,许是香火旺盛的缘故,那张肃穆的金面上好像渗出了些油光,莲花座也仿佛透着金光,贡台上香烛果品常年不断,凛冽的寒风吹进殿内,香烟缭绕,唬住了前来祈愿的人。
虽然火葬已经不算罕见,我还是来到这里为母亲做最后的事情,她该是跟过一个又一个男人,却始终没能找到归宿,最后堕落瘫痪在那张塞满棉被发着汗骚腥味的土炕上,染上了一身的恶毒,我朝着佛祖一头磕了下去,额头抵住大殿冰凉的磨石地上。
我想起那几枚洗不干净的大洋,眼泪顺着鼻尖滴了下来。
关键词: